Nature Biotechnology:血液中的“肠道私语”:一种颠覆性的癌症检测方法正在浮现
2025-07-13 生物探索 生物探索 发表于上海
研究发现,通过检测血浆中微生物游离 RNA 的修饰特征,可精准诊断结直肠癌,其区分癌症与健康样本的 AUC 值达 0.98,尤其对早期癌症识别能力突出。
引言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生活着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隐形帝国”?这个帝国由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组成,它们主要“定居”在我们的肠道中,构成了我们独特的肠道微生物组(microbiome)。长期以来,我们视它们为简单的“过客”,但现代医学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揭示,这个帝国不仅不是沉默的,反而时刻与我们的身体进行着复杂的“对话”。它们的兴衰、它们的“情绪”,甚至它们的“口音”,都与我们的健康,尤其是癌症的发生,息息相关。
在癌症的战场上,医生和研究人员们一直在寻找一种理想的武器:一种能够在癌症萌芽之初就精准发现其踪迹的方法。传统的组织活检(tissue biopsy)虽然是金标准,但它具有侵入性,过程痛苦,且难以用于早期筛查。近年来,“液体活检”(liquid biopsy)的概念横空出世,点燃了新的希望。它试图通过分析血液等体液中的肿瘤“蛛丝马迹”——如肿瘤细胞脱落的DNA碎片,即游离DNA(cell-free DNA, cfDNA)——来实现对癌症的非侵入性诊断。然而,这把利器也并非完美无瑕。在癌症早期,肿瘤释放到血液中的cfDNA信号极其微弱,如同在喧闹的城市中寻找一根掉落的针,这使得早期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一直面临着巨大挑战。
7月8日,发表在《Nature Biotechnology》上的研究“Modifications of microbiome-derived cell-free RNA in plasma discriminates colorectal cancer samples”,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角。该研究将侦测的焦点从人类自身的DNA,巧妙地转向了我们体内那些微生物“房客”的RNA,更准确地说,是这些RNA上的“秘密标记”。研究人员发现,通过“窃听”这些来自肠道微生物的“私语”,并解读其在癌症影响下变化的“口音”,他们能够以惊人的准确性“揪出”早期的结直肠癌。这不仅是一项技术的突破,更可能开启一个通过解读“人-微”共生关系来诊断疾病的全新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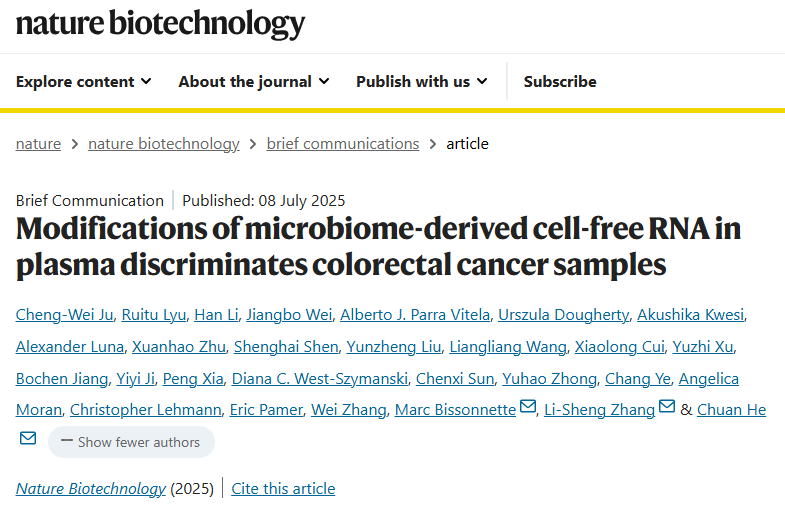
血液中的“幽灵信使”:为何DNA不够,RNA来凑?
要理解这项研究的颠覆性,我们首先要回到液体活检的核心挑战。想象一下,一个早期的肿瘤,可能只有几毫米大小,它释放到全身几升血液中的cfDNA分子少之又少。传统的液体活检技术就像一个侦探,试图在巨大的信息海洋中找到这几个来自罪犯的“指纹”。这在技术上极其困难,导致很多早期癌症患者的检测结果呈假阴性,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机。
此外,人体的衰老和正常组织的新陈代谢也会向血液中释放cfDNA,这些“良民”的DNA与来自肿瘤的DNA混杂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背景噪音,进一步干扰了侦探的判断。面对这一困境,研究人员开始思考:除了DNA,血液中是否还漂浮着其他更灵敏的“信使”?
他们的目光投向了DNA的“工作伙伴”——RNA。
如果说DNA是细胞的“设计蓝图”,记录着生命体的全部遗传信息,那么RNA就是根据这份蓝图发出的“实时工作指令”。细胞的每时每刻的活动,比如蛋白质的合成、能量的代谢,都由成千上万的RNA分子在精确调控。因此,RNA更能动态地反映细胞当下的生理或病理状态。一个癌细胞和一个正常细胞,它们的“工作指令”必然大相径庭。
研究人员从健康人和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患者的血浆中,成功分离出了这些漂浮的游离RNA(cell-free RNA, cfRNA)。通过高分辨率的生物分析仪检测,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cfRNA并非完整的长链,而是大多以非常短的片段形式存在,长度集中在50个核苷酸(nt)左右。这个尺寸,恰好与一类在细胞中负责搬运氨基酸的RNA——转运RNA(transfer RNA, tRNA)——非常相似。
这一发现至关重要。tRNA分子具有非常稳定、折叠紧密的三维结构,就像一个坚固的“旅行箱”,这使得它比其他线性的RNA(如信使RNA, mRNA)更能抵抗血液中各种酶的降解。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恶劣的血液环境中,我们依然能捕捉到大量的tRNA及其片段。它们就像是细胞凋亡或坏死后散落的、最坚固耐用的“遗物”。研究人员推测,这些在血液中稳定存在的cfRNA,尤其是tRNA,可能携带着比cfDNA更丰富的疾病信息。
但真正让研究人员兴奋的,并非RNA序列本身,而是隐藏在序列之上的另一层信息密码——RNA修饰(RNA modification)。
这就像我们读书时,会在重要的句子下面划线,在段落旁边做批注,或者给某个词打上星号。这些标记虽然没有改变文字本身,却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信息的理解和处理方式。RNA分子在细胞中同样会被进行各种各样的“标记”,比如在某个碱基上添加一个甲基(methylation),这些化学修饰会影响RNA的稳定性、功能及其与其他分子的相互作用。据统计,已知的RNA修饰超过170种。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癌细胞或肿瘤微环境中的细胞,其RNA上的“标记”模式是否会与正常细胞不同?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些独特的“标记”模式,将成为比DNA序列更灵敏、更特异的癌症生物标志物。这就好比,罪犯不仅留下了指纹(DNA),还留下了一张写有独特暗号的字条(RNA修饰),而破译这个暗号,将是抓到他的关键。
然而,破译这个“暗号”面临一个巨大的技术瓶颈。许多RNA修饰,特别是甲基化修饰,会像路障一样,阻断常规测序技术中负责读取RNA序列的“阅读器”——逆转录酶。这使得我们无法获得完整的序列信息,更不用说准确定位和量化这些修饰了。要实现他们的设想,研究人员必须先打造一把能“越过路障”并“读懂暗号”的神奇钥匙。
LIME-seq:一把能破译微生物“摩斯密码”的神奇钥匙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该研究团队开发并优化了一种名为“低起始量多重甲基化测序”(low-input multiple methylation sequencing, LIME-seq)的技术。这项技术的核心,在于选择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阅读器”——来自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逆转录酶。
大多数逆转录酶在遇到RNA修饰位点时会“卡壳”或脱落,导致测序失败。但HIV逆转录酶却与众不同,它具有一种“越障”能力,能够强行读过这些修饰位点。更有趣的是,在读过这些“路障”时,它虽然不会停下,但有很大概率会“犯个小错”,即在对应位置合成一个错误的DNA碱基。
这个“错误”正是LIME-seq技术的精髓所在!研究人员将这个看似是缺陷的特性,转化为一个强大的信号。他们不再害怕酶的“失误”,反而主动去捕捉这些“失误”。通过深度测序,如果在某个特定位点,大量测序读数都显示出从A到G的突变,那就强烈暗示原始的RNA分子在这个A位点上存在一个修饰。
这个过程就像一位侦探在检查一份电报,发现其中某些字母被打成了另一种摩斯密码。他意识到,这并非乱码,而是发报人故意留下的“暗号”。LIME-seq技术就是这样,它将RNA修饰这个物理信号,巧妙地转换成了测序数据中可被精确量化的突变信号。更重要的是,通过计算突变读数占总读数的比例,LIME-seq还能定量分析出该位点被修饰的化学计量比(stoichiometry),即有多少比例的RNA分子在这个位置上被“做了标记”。
为了验证这把“钥匙”是否可靠,研究人员首先在实验室常用的肝癌细胞系(HepG2)中进行了测试。他们提取了细胞中的小RNA,用LIME-seq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该技术重复性极高,两次独立实验检测到的修饰谱,其相关性系数(r值)高达0.990(1代表完全一致)。此外,即便是将RNA起始量从50纳克(ng)降低到1.5纳克,不同起始量之间的检测结果依然高度一致(r值大于0.96)。这证明LIME-seq不仅精准,而且极其灵敏,足以处理临床样本中极其微量的cfRNA。
手握这把强大的“解码钥匙”,研究人员终于可以开始探索血液中那些“幽灵信使”的秘密了。
惊人发现:血液中近40%的“悄悄话”竟来自肠道菌群!
当研究人员将LIME-seq技术应用于36名健康人的血浆cfRNA样本时,一个完全出乎他们意料的结果出现了。
按照常规思路,血浆中的cfRNA应主要来源于人体自身的细胞。测序数据经过处理后,确实有大约60-80%的读数能够比对到人类基因组上,其中tRNA和核糖体RNA(rRNA)的片段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与他们最初的观察相符。
然而,剩下的20-40%的测序读数,却在人类基因组中找不到“归宿”。它们成了“神秘序列”。研究人员并未放弃对这些序列的追寻,他们将这些序列与一个庞大的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进行比对。结果令人震惊:这些“神秘序列”绝大部分都来自于细菌!
这意味着,在我们的血液中,除了有人类细胞的“遗言”,还漂浮着大量来自微生物的“悄悄话”。这些微生物cfRNA的片段长度同样很短,集中在30-50个核苷酸,主要也是tRNA和rRNA的片段。通过进一步的物种鉴定,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微生物RNA主要来源于几个特定的细菌“大家族”,如芽孢杆菌目(Bacillales)、黄单胞菌目(Xanthomonadales)、伯克氏菌目(Burkholderiales)等。这些都是我们肠道微生物组中的常见成员。
这个发现颠覆了传统认知。我们的肠道虽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但肠道屏障并非坚不可摧。肠道中的微生物在生老病死、与宿主细胞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其细胞内容物,包括RNA,完全有可能“泄漏”到血液循环中。我们的血液,原来是一个比想象中更热闹的“信息交流中心”,是宿主与微生物共生体之间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
但一个严谨的研究人员必须排除所有可能的干扰。会不会是抽血时,皮肤上的细菌污染了样本?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人员进行了一个巧妙的对照实验。他们用同一根针头,从同一个人身上连续抽取了多管血液。如果污染主要来自皮肤,那么第一管血中的微生物信号应该最强,后续会逐渐减弱。但实验结果显示,多管血液样本的微生物谱高度一致。这有力地证明了,血液中的微生物RNA信号是真实存在的全身性信号,而非简单的局部污染。
至此,研究人员的眼前展现出了一幅全新的图景。他们不仅可以分析来自宿主(host)的cfRNA信号,还能同时监测来自微生物组(microbiome)的cfRNA信号。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在诊断结直肠癌时,究竟谁才是更可靠的“线人”?是人体自身的信号,还是这些肠道“房客”的信号?
终极对决:人类信号 vs. 微生物信号,谁是揪出癌症的“神探”?
研究团队招募了27名结直肠癌(CRC)患者和36名健康对照者,利用LIME-seq技术对他们血浆中的cfRNA进行了全面分析,一场“终极对决”就此拉开帷幕。
人类信号的表现
首先,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人类基因组的cfRNA。他们发现,与健康人相比,CRC患者血浆中确实有一些人类RNA的丰度发生了变化,涉及约253个人类基因。同时,在人类tRNA的某些特定位点上,RNA修饰水平也存在差异。
这看起来很有希望。然而,当研究人员利用这些人类cfRNA的丰度和修饰数据,建立一个机器学习模型来区分癌症和健康样本时,结果却不尽人意。尤其是一个基于人类tRNA修饰特征构建的分类器,其表现非常平庸,其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值仅为0.55。
AUC是评估诊断模型性能的金标准。AUC值为1代表完美诊断,0.5代表完全随机的猜测(相当于抛硬币)。0.55这个数值,意味着该模型几乎没有区分能力。
为什么会这样?研究人员推测,血液中的人类cfRNA来源太复杂了。它们可能来自肝脏、肌肉、免疫细胞等全身各种组织,而不仅仅是结肠的肿瘤。这些来自非肿瘤组织的“噪音”信号,极大地稀释和掩盖了来自肿瘤的、真正有价值的“癌症信号”,使得模型难以做出准确判断。
微生物信号的初次登场
在人类信号“折戟”后,研究人员将希望转向了微生物信号。大量前期研究已经证实,肠道微生物组的失调与结直肠癌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例如,某些特定菌群的异常增多,被认为是CRC的风险因素。
研究人员首先尝试了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仅利用微生物cfRNA的丰度(abundance)信息。也就是说,他们只看哪些菌的RNA在CRC患者血液中更多或更少。他们基于这些丰度数据建立了一个分类模型。这一次,结果有了显著提升,模型的AUC值达到了0.77。
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证明了血液中的微生物RNA丰度确实能反映出结直肠癌的存在。它优于随机猜测,也比基于人类tRNA修饰的模型好得多。但这对于一个可靠的临床诊断工具来说,还远远不够。一个AUC为0.77的模型,在实际应用中仍然会有相当高的误诊率。
简单的丰度信息,似乎还不足以揭示故事的全貌。这促使研究人员祭出了他们的“终极武器”——微生物RNA的修饰信息。
破案关键:癌症如何改变了微生物的“口音”?
研究人员的核心假设是:癌症的存在,会给肠道微生物带来巨大的环境压力,从而改变它们的代谢活动和基因表达,最终体现为它们RNA修饰模式的系统性改变。
这就好比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充满压力的环境中,他的说话方式、语调甚至口音都可能不自觉地发生变化。RNA修饰,就是微生物的“口音”。研究人员要做的,就是去聆听并分辨这种因癌症而改变的“口音”。
他们将LIME-seq检测到的、成千上万个微生物RNA修饰位点的定量信息,作为特征输入到一个更复杂的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模型中。SVM是一种强大的分类算法,它能在高维数据空间中找到一个最优的“分界线”(超平面),将癌症样本和健康样本最清晰地分离开。
当模型的训练和验证结果出来时,所有人都被震撼了。
这个基于微生物cfRNA修饰特征的模型,在区分CRC患者和健康对照时,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性能,其AUC值飙升至惊人的0.98!
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数值。它不仅远远超过了基于人类信号的AUC=0.55,也碾压了仅基于微生物丰度的AUC=0.77。在交叉验证中,该模型的整体准确率达到了95%,在最优阈值下,其灵敏度(正确识别出癌症患者的能力)为93%,特异性(正确识别出健康人的能力)为92%。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目前临床上已获美国FDA批准的、用于结直肠癌血液筛查的SEPT9基因甲基化检测,其灵敏度大约在70%左右。而这项新技术,尤其是其高达93%的灵敏度,意味着它有潜力发现更多真正的癌症患者,显著减少漏诊。
更令人振奋的是,这种高准确性在癌症的极早期阶段同样有效。分析显示,无论是原位癌(Stage 0)还是I期癌症,该模型都能以极高的概率将其成功识别。这恰恰解决了传统液体活检最大的痛点——早期诊断能力不足。通过聆听微生物的“口音”变化,研究人员似乎找到了那把能打开早期癌症诊断大门的钥匙。
这项研究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利用了生物系统的一个基本原理:应激反应。肿瘤微环境对微生物而言是一种强烈的“应激源”,而RNA修饰是细胞(包括细菌细胞)响应应激的核心机制之一。因此,检测RNA修饰的变化,本质上是在检测微生物对癌症存在的“生物反应”,这比单纯检测肿瘤自身脱落的物质(cfDNA)要灵敏得多。这就像通过观察一群鸟是否惊飞,来判断草丛里是否藏着猛兽,远比直接看到猛兽本身要容易和迅速。
揭秘“关键线人”:哪些菌群在为癌症“通风报信”?
一个AUC高达0.98的模型固然强大,但它也像一个“黑箱”,我们只知道它能做出准确判断,却不清楚它是依据哪些线索。为了打开这个“黑箱”,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名为SHAP(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的分析方法。这个工具可以评估模型中每一个特征(即每一个微生物RNA修饰位点)对最终预测结果的贡献度,从而告诉我们,哪些菌的哪个“口音”变化,是区分癌症的“关键线人”。
分析结果揭示了一些与已知生物学知识高度吻合的“关键菌群”:
伯克氏菌科(Burkholderiaceae):该家族成员的RNA甲基化水平在CRC患者中显著上调。这类细菌通常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病原体,在免疫力低下或环境失调时可能引发问题。
梭菌科(Clostridiaceae):与前者相反,该家族成员的RNA甲基化水平在CRC患者中显著下调。有趣的是,某些梭菌(如溶癌梭菌)因其靶向肿瘤缺氧区域的能力,正被研究作为一种新型的抗癌疗法。
微杆菌科(Microbacteriaceae):其成员的RNA甲基化水平也呈现上调。这类细菌同样与免疫功能受损个体的感染有关。
此外,该模型还重点识别出了几种已在多项研究中被证实与CRC密切相关的细菌,如厌氧消化链球菌(Peptostreptococcus anaerobius)、中间普雷沃氏菌(Prevotella intermedia)和微小微单胞菌(Parvimonas micra)。LIME-seq数据显示,在CRC患者中,这些特定细菌的cfRNA上的修饰水平(体现为突变率)显著高于健康人。
这些发现意义非凡。它不仅验证了模型的生物学合理性,还将抽象的AI预测与具体的微生物学知识联系起来。这表明,模型并非基于某些随机的统计巧合,而是真实地捕捉到了与CRC病理生理过程相关的微生物功能变化。我们不仅知道“谁”在报警,还知道它们是如何“报警”的。
不止于肠癌:我们是否推开了一扇疾病诊断新世界的大门?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为结直肠癌提供了一种新的筛查工具。它更像是一次“范式转移”,为我们理解和诊断疾病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首先,这项技术的临床实用性得到了初步验证。在真实的临床环境中,血液样本从采集到处理往往需要一定时间。研究人员模拟了这一场景,将血液样本在4°C下分别储存了2小时、8小时和24小时。结果显示,微生物cfRNA的修饰信号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即使在储存8小时后,其信号谱与新鲜样本的相关性依然高达0.9以上;24小时后,相关性也维持在0.85以上。相比之下,人类自身的cfRNA信号则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这种稳定性,对于未来将该技术转化为标准化的临床检测至关重要。
其次,该方法的应用潜力可能超越结直肠癌。为了探索其普适性,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小规模的初步研究,将该模型应用于一种与肠道不直接相关的癌症——胰腺癌(pancreatic cancer, PANC)。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样本量很小(7名胰腺癌患者 vs 8名健康人),基于微生物cfRNA修饰的模型,依然能够清晰地将两组人群区分开来。这暗示着,不同类型的癌症,即使病灶位置遥远,也可能通过某种系统性的机制(如炎症反应)对肠道微生物组产生深远影响,而这种影响,可以被血液中的微生物“口音”所捕捉。
最后,这项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人-微共生体”健康状态的窗户。我们的身体并非一个孤立的系统,而是与体内数万亿微生物共同构成的一个“超级有机体”。微生物的健康,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延伸。微生物的“不安”,往往预示着宿主正面临着疾病的威胁。LIME-seq技术,就像一个超高灵敏度的“听诊器”,让我们第一次能够如此清晰地听到来自这个“第二基因组”的信号。
未来,这项技术或许不仅能用于癌症诊断,还可能应用于其他与肠道菌群失调相关的疾病,如炎症性肠病(IBD)、自身免疫病、甚至代谢性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早期预警和监控。通过解读血液中这些“肠道私语”,我们或许能以前所未有的视角,洞察疾病的发生机制,并实现真正的个性化精准医疗。
当然,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诞生,从实验室走向临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项研究的样本量相对有限,还需要在更大规模、更多样化的人群中进行验证。但它无疑已经为我们指明了一个无比激动人心的方向:在我们与体内微生物的古老共生关系中,蕴藏着解读健康与疾病的终极密码。而现在,我们终于开始学着去倾听了。
参考文献
Ju CW, Lyu R, Li H, Wei J, Parra Vitela AJ, Dougherty U, Kwesi A, Luna A, Zhu X, Shen S, Liu Y, Wang L, Cui X, Xu Y, Jiang B, Ji Y, Xia P, West-Szymanski DC, Sun C, Zhong Y, Ye C, Moran A, Lehmann C, Pamer E, Zhang W, Bissonnette M, Zhang LS, He C. Modifications of microbiome-derived cell-free RNA in plasma discriminates colorectal cancer samples. Nat Biotechnol. 2025 Jul 8. doi: 10.1038/s41587-025-02731-8.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0629040.
本网站所有内容来源注明为“梅斯医学”或“MedSci原创”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梅斯医学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为“梅斯医学”。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或“梅斯号”自媒体发布的文章,仅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站仅负责审核内容合规,其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不负责内容的准确性和版权。如果存在侵权、或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在此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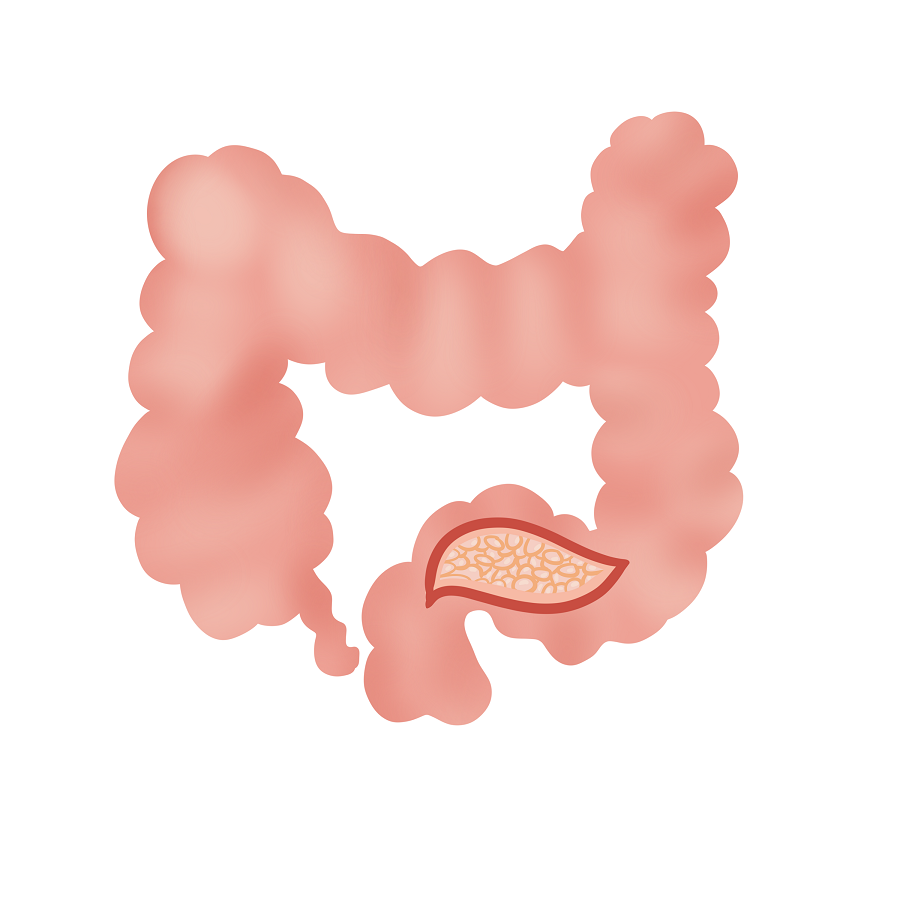











#结直肠癌# #液体活检#
7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