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Medicine:如何用“病理学GPT”颠覆肺癌诊断,让三周等待缩短为44分钟?
2025-07-16 生物探索 生物探索 发表于上海
EAGLE 模型可快速从肺腺癌病理切片中检测 EGFR 突变,泛化能力强,优化诊断流程,减少检测需求,具临床转化价值。
引言
在现代医学的宏伟叙事中,没有什么比“等待”二字更让人揪心。当一份可能预示着命运转折的活检样本被送入实验室后,患者和家属便开始了漫长而焦虑的倒计时。对于全球头号癌症杀手——肺癌,尤其是其最常见的类型“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 LUAD)”,这份等待的结果往往决定着后续的治疗方案,乃至生命的长度。
精准医疗的时代,我们已经知道,并非所有肺腺癌都千篇一律。一部分患者的肿瘤细胞中,存在着“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的基因突变。这个突变就像一个失控的“油门”,让癌细胞疯狂增殖。幸运的是,研究人员研发出了能够精准“踩刹车”的靶向药——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用对了药,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将得到显著改善。因此,准确、快速地检测出EGFR突变,成为了肺腺癌患者开启正确治疗的第一把,也是最关键的一把钥匙。
然而,这把钥匙的获取过程却充满了挑战与妥协。传统的检测方法如同两位性格迥异的赛跑选手:一位是追求速度的“短跑健将”,另一位是追求全面的“马拉松冠军”,但两者都非完美。我们常常不得不在速度、准确性和宝贵的肿瘤组织之间做出艰难的权衡。
就在这个困局之中,7月9日发表在《Nature Medicine》上的重磅研究“Real-world deployment of a fine-tuned pathology foundation model for lung cancer biomarker detection”,为我们带来了破局的曙光。该研究介绍了一位全新的“AI神探”——EAGLE模型。它仅凭一张普通的病理切片,就能在短短44分钟内嗅出EGFR突变的蛛丝马迹,其表现不仅在实验室中令人惊艳,更在真实的临床世界里通过了严苛的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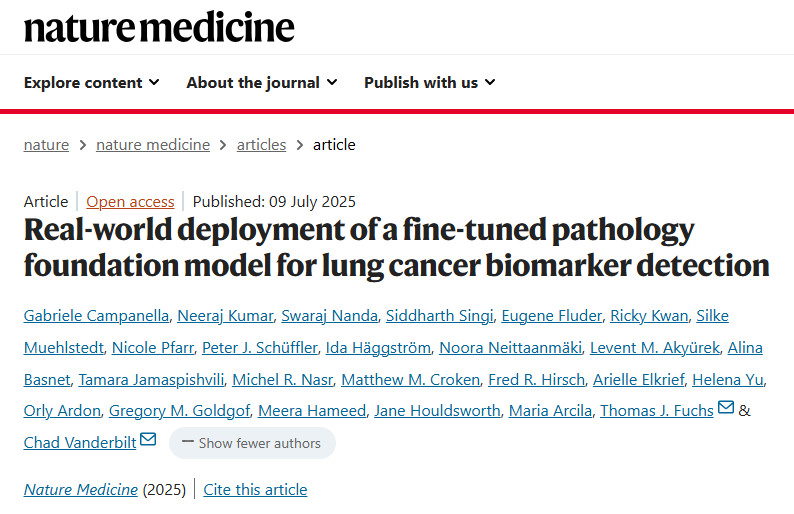
精准医疗“高速公路”上的世纪难题:一张病理切片背后的生命博弈
要理解EAGLE模型的革命性,我们必须先走进它试图解决的那个“战场”——现代肺癌分子病理诊断的真实世界。这里没有硝烟,却充满了对时间、资源和信息的激烈争夺。
“油门”与“刹车”:EGFR突变的关键意义
首先,让我们把复杂的分子生物学概念变得形象一些。想象一下,正常的EGFR基因就像汽车里一个功能完好的油门踏板,它接收大脑(细胞信号)的指令,精确控制着细胞的生长和分裂速度。然而,当EGFR基因发生突变时,这个油门踏板就好像被卡住了,持续不断地向引擎(细胞增殖机制)发送“加速”信号,导致癌细胞无法控制地生长,最终形成肿瘤。
而靶向药物TKI,就是专门为这个“卡住的油门”量身定制的“智能刹车系统”。它能精准地识别并作用于突变的EGFR蛋白,切断其失控的信号,从而有效抑制肿瘤生长。这种治疗方式效果显著,副作用相比传统化疗也更小。但前提是——必须确认病人的“油门”确实是EGFR这一款,并且确实“卡住了”。如果用错了刹车,不仅毫无效果,还会耽误宝贵的治疗时机。
因此,临床指南明确要求,对于所有晚期(IB期及以上)的肺腺癌患者,进行EGFR突变检测是必需的。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鸿沟。研究数据显示,即便在美国这样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仍有高达24%至28%的肺腺癌患者未能接受EGFR检测。在全球更多地区,这个比例只会更高。成千上万的患者,每年都因此与最适合他们的“一线生机”失之交臂。
这背后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我们现有的检测工具链存在着一个看似难以调和的“三体问题”:速度、准确度和组织样本量,这三者我们总想兼得,却往往事与愿违。
检测工具的“两难选择”:短跑选手 vs. 马拉松冠军
目前,临床上有两种主流的EGFR检测方法,它们各自代表了一种诊断哲学。
“短跑选手”——基于PCR的快速检测
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是一种快速、靶向的检测技术。它的原理好比是拿着一本“已知通缉犯名册”(常见的EGFR突变类型),去样本中快速筛查是否存在这些“通缉犯”。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速度极快,通常在1到3天内就能出结果。
然而,它的缺点同样明显。首先,它是一项“有损检测”。为了提取DNA,需要从珍贵的活检组织块上刮取一部分细胞,这意味着本就稀缺的“原材料”被消耗了。其次,它的视野有限。名册上没有的“新型罪犯”(不常见的EGFR突变,例如许多外显子20插入突变)它就识别不出来。这导致其技术灵敏度通常在85%至90%之间。该研究中也提到,根据他们的经验,这种检测的阴性预测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约为90%至95%,这意味着在那些被报告为“阴性”(未检测到突变)的样本中,实际上仍有5%到10%的患者携带着可靶向的EGFR突变。他们本应接受TKI治疗,却因为检测的局限性而被错误地归入“不适合”的行列,从而接受了次优的治疗方案。
“马拉松冠军”——二代测序 (NGS)
二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则是截然不同的思路。它不再是按图索骥,而是试图绘制出整个区域的“详细地图”,对EGFR基因甚至数百个与癌症相关的基因进行全面测序。这使得它能够发现各种已知和未知的突变,准确性极高。
但这位“马拉松冠军”的耐力是以牺牲速度为代价的。一个完整的NGS流程,从样本送到出具报告,通常需要2到3周的时间。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患者的病情可能发生变化,治疗窗口期被一再压缩。
更致命的是,NGS对“原材料”的要求更高。它需要足够数量和质量的DNA才能成功运行。而悲剧在于,很多时候,当一份活检组织经历了诊断、免疫组化(用于区分癌症类型)、以及前面提到的PCR快速检测等多轮消耗后,等到准备进行NGS时,已经“弹尽粮绝”。研究指出,高达25%的样本会因为组织量不足而导致NGS检测失败。病人不得不承受再次活检的风险和痛苦,或者干脆放弃这一最全面的检测。
病理科医生的“索菲的选择”
至此,我们看到了临床实践中的困境:选择快速PCR?你能迅速得到结果,但可能牺牲了10%的准确性,并且消耗了组织,增加了后续NGS失败的风险。直接上NGS?你能获得最全面的信息,但需要忍受数周的等待,而且一开始就可能因为组织不够而失败。
这就像一个病理科医生面临的“索菲的选择”,每一步决策都牵动着患者的命运。正是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妥协的背景下,研究人员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开辟第三条道路?一条既能保持高速,又不消耗组织,还能为最终的“金标准”检测保驾护航的道路?
EAGLE模型,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诞生的。
AI“神探”:如何用海量数据,教会机器看懂细胞的“悄悄话”?
当人类的肉眼和传统技术遭遇瓶颈时,我们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一个大胆而迷人的设想浮出水面:既然基因突变会改变细胞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上的改变,是否会在细胞的形态、大小、排列方式等视觉特征上留下微妙的“指纹”?一个足够强大的AI,能否通过“阅读”这些细胞的“悄悄话”,直接从标准的病理切片图像中推断出其背后的基因秘密?
这正是EAGLE模型的核心使命。但要将这个想法变为现实,绝非易事。它需要一位训练有素的“老师”和一套巧妙的“教学方法”。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病理学“GPT”——基础模型的力量
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最激动人心的突破之一,莫过于“基础模型(Foundation Model)”的崛起。我们熟知的ChatGPT就是基于大型语言基础模型GPT系列构建的。这些模型通过在海量的文本数据上进行“预训练”,学会了语言的通用规律和逻辑,从而能够轻松地适应各种下游任务,如翻译、写作、对话等。
EAGLE的研究人员巧妙地将这一思想“移植”到了病理学领域。他们没有从零开始构建一个AI模型,而是选择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个“巨人”,是一个名为Prov-GigaPath的病理学基础模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病理学界的GPT”。它已经“阅读”了数百万张各种类型的病理图像,虽然它还不认识什么是“EGFR突变”,但它已经对细胞核的形态、细胞质的颜色、腺体结构的排列等病理学的“基本词汇”和“语法”了如指掌。它拥有了对病理图像的通用理解能力。
这种“预训练”的优势是巨大的。它意味着EAGLE的起点,已经远超那些“从零学起”的AI模型。它不必再费力去学习区分细胞核和背景,而是可以直接进入更高级的学习阶段。
“因材施教”:针对EGFR的精细调优
有了这位博学的“通才”老师Prov-GigaPath,下一步就是把它培养成一位专注于EGFR突变的“专才”。这个过程被称为“精细调优(Fine-tuning)”。
研究人员为此准备了一份量身定制的“教科书”——一个庞大的、来自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SKCC) 的临床数据集。这份“教科书”包含了5,174张肺腺癌患者的数字化病理切片。每一张切片,都配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标签”:通过NGS检测确定的,该患者的肿瘤是否存在EGFR突变。
训练过程就像这样:模型会像像素描一样,将高分辨率的数字病理切片分解成数万个小图块,高效地从每个小图块中提取出丰富的形态学特征。接下来,一个巧妙的“注意力机制”聚合器会登场,它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侦探长,审视着手下成千上万个“侦探”提交的线索,给那些最可能包含EGFR突变“指纹”的区域更高的“注意力权重”,然后综合所有线索,给出一个最终的概率分数。模型给出判断后,会与真实的NGS结果进行比对,如果猜错了,一个名为“反向传播”的算法会启动,微调其内部的数亿个参数,让它在下一次遇到类似情况时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这个过程在24块顶级的NVIDIA H100 GPU上并行进行,历时约9.3小时,迭代了20个周期。最终,一个能识别EGFR突变“视觉指纹”的AI神探——EAGLE,诞生了。它不需要消耗任何物理组织,只需要一份病理图像的数字拷贝,就能在几分钟内完成一次“虚拟”的分子诊断。
这位新晋“神探”的能力究竟如何?它能否走出象牙塔,在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中证明自己?
从实验室到真实世界:AI模型的“终极压力测试”
一个AI模型,在训练它的“母校”——即原始数据来源的机构——表现出色,这并不足为奇。真正的考验在于,当它面对来自不同医院、由不同技师处理、被不同扫描仪数字化的“陌生”切片时,是否还能保持同样敏锐的“嗅觉”。这考验的是模型的“泛化能力(generalization)”,也是它能否从一个酷炫的“科研玩具”转变为一个可靠的“临床工具”的关键。
EAGLE的研究团队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为模型设计了一场堪称“地狱级”的全球巡回大考。
第一关:跨机构、跨设备的“大联考”
首先是一系列严格的回顾性验证,即用已经存在的、带有已知答案的数据集来测试模型。
“校内摸底考”——内部验证:研究人员首先在MSKCC内部,用一个全新的、包含1,742张切片的验证集对EAGLE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模型的表现相当稳健,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达到了0.847。AUC是一个衡量模型综合诊断能力的指标,值越接近1,表示模型区分“有突变”和“无突变”的能力越强。0.847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证明模型在“主场”作战时基本功扎实。
“全球巡回赛”——外部验证:这才是真正的挑战。研究团队收集了来自四大洲不同机构的数据集,它们代表了真实世界的多样性,包括美国的西奈山卫生系统(MSHS),欧洲的瑞典萨尔格伦斯卡大学医院(SUH)和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TUM),以及一个庞大的公共数据库——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在这些总计1,484张“客场”切片上,EAGLE的总体AUC达到了惊人的0.870,甚至略高于其在“主场”的表现!这有力地证明了EAGLE的强大泛化能力。
“驾照路考”——多扫描仪测试:为了进一步排除设备差异的干扰,研究人员还进行了一项巧妙的实验。他们将来自MSHS的同一批切片,分别用三种不同品牌和型号的病理扫描仪进行数字化。结果显示,不同扫描仪生成的图像所对应的模型预测分数之间,具有高度的线性相关性(皮尔逊相关系数在0.828到0.935之间)。这意味着EAGLE通过了“路考”,它不会因为换了辆“车”(扫描仪)就不会“开”(分析)了。
这一系列的测试,如同层层加码的关卡,EAGLE都成功闯过。它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个只能在特定条件下生存的“温室花朵”,而是一个能够适应真实世界复杂环境的“野战兵”。但研究人员并未就此止步,他们决定将挑战推向顶峰——进行一场实时的、前瞻性的“终极实战演习”。
终极考验:前瞻性“静默试验”
这就是论文标题中“Real-world deployment”的精髓所在。研究团队在MSKCC开展了一项为期4个月的“静默试验(silent trial)”。它的运作模式是:当临床上有一例新的肺腺癌患者活检样本按正常流程被扫描和诊断时,EAGLE系统会在后台被自动触发,实时地对这张全新的、模型前所未见的数字切片进行分析,并生成一个EGFR突变预测结果。然而,这个结果是“静默”的,它会被秘密记录下来,而不会展示给临床医生,也绝不会影响该患者的实际诊疗决策。
等到数天或数周后,当标准的分子检测结果出来时,研究人员再将EAGLE的“秘密预测”与这个“金标准答案”进行比对。这种方式的意义在于,它完全模拟了AI在未来临床应用中的真实场景,排除了所有回顾性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数据筛选偏倚。
在这场终极实战演习中,EAGLE分析了197例原发性肿瘤样本。结果令人振奋:其AUC达到了0.890!这一数据不仅与之前的回顾性测试结果高度一致,甚至表现更佳。它证明了:EAGLE模型已经准备好了。它已经具备了在真实临床环境中稳定、可靠地工作的能力。
至此,EAGLE模型已经通过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所有考验。现在,是时候看看这位神探的到来,将如何改写现有战场的规则了。
重塑规则:AI如何将三周的等待缩短为44分钟?
EAGLE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能“看”出基因突变。它最大的潜力,在于能够作为一个强大的“智能调度员”,优化整个肺癌分子诊断的流程,打破前文所述的速度、准确性和组织样本量之间的“不可能三角”。
速度的革命:从半个月到一杯咖啡的时间
让我们先来看一组直观的时间对比。在MSKCC的真实工作流中,各项检测出具报告的中位时间是:
- NGS (MSK-IMPACT) 检测:435.26小时(约18天)
- PCR快速检测 (Idylla):48.78小时(约2天)
- EAGLE模型预测:0.74小时,也就是44分钟
这个对比是颠覆性的。从超过半个月的漫长等待,到两天,再到不足一个小时。这意味着,在病理医生完成初步诊断、将切片数字化的那一刻起,不到一小时,一个关于EGFR状态的高精度预测结果就已经可以摆在他的面前。这个信息来得如此之早,以至于它可以指导后续所有的检测决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动地等待一个又一个检测结果。
AI辅助工作流:更聪明地使用“弹药”
基于这种速度优势,研究人员设计了一套全新的、由AI辅助的诊断工作流程。这个流程的核心思想是:用AI的免费、快速、无损预测,来决定是否需要启动昂贵、缓慢、有损的分子检测。
具体流程如下:首先,EAGLE进行“预筛查”,当一张新的肺腺癌数字切片产生后,EAGLE立即进行分析,并给出一个EGFR突变概率分值。然后,进行智能分流:
情况一:高概率阴性。如果EAGLE的预测分数极低,模型非常有信心地认为“该样本不含EGFR突变”。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可以建议跳过PCR快速检测。这不仅节省了时间和金钱,更重要的是,完整地保留了组织样本,为后续必须进行的NGS检测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情况二:高概率阳性。如果EAGLE的预测分数极高,模型非常有信心地认为“该样本含有EGFR突变”。同样,系统可以建议跳过PCR快速检测。因为最终确诊和分型仍然依赖NGS,AI的预测已经提供了足够强的证据,可以直接等待NGS的精细报告。这一步也为NGS保留了宝贵的组织。
情况三:不确定区域。如果EAGLE的预测分数落在了两个阈值之间,表示AI也“拿不准”。在这种“灰色地带”,系统则建议按照传统流程,进行PCR快速检测,以获取更多信息。
令人惊叹的效率提升:具体数据解读
这套新流程的效果如何?通过调整两个阈值的松紧,可以在“维持现有诊断标准性能”的前提下,实现不同程度的效率提升。研究人员在静默试验中验证了三个预设的策略:
最保守策略下,能减少17.8%的PCR快速检测需求;中间策略下,可以减少37.1%的PCR检测;而在最积极(但仍安全)的策略下,PCR快速检测的需求被惊人地减少了43.1%!同时,整个流程的诊断性能仍然与单独使用PCR快速检测的历史数据相当。这意味着,近一半的PCR检测都可以被安全地省去!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对于医院和医保系统,它意味着成本的降低。对于病理科,它意味着工作流程的简化和效率的提升。而对于患者,它的意义最为重大:减少了等待时间,保护了珍贵的组织,并大大降低了因组织耗尽导致NGS失败的风险。
EAGLE模型,就像一个精明的军事参谋,它不上前线冲锋,而是通过卓越的情报分析和资源调度,让整个战役的效率和胜率都得到了质的飞跃。
当AI“侦探”犯错:揭开“黑箱”,我们能学到什么?
在为AI的惊人能力欢呼的同时,一个理性的声音总会响起:AI是完美的吗?它会犯错吗?当它犯错时,我们能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所谓的“黑箱”问题,也是所有临床AI应用必须面对的灵魂拷问。
EAGLE的研究团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反而通过巧妙的设计,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位AI神探的“内心世界”,从它的“失误”中学习到宝贵的经验。
“注意力地图”:让AI的思考过程可视化
为了理解EAGLE的决策逻辑,研究人员生成了“注意力地图(attention maps)”。这张图谱用热力图的形式,在原始的病理切片上标记出模型在做决策时,究竟“看”了哪些区域,以及对这些区域的重视程度。红色区域代表“高度关注”,蓝色区域则代表“基本忽略”。这就像是给AI侦探配备了一支“荧光笔”,让它在勘察完“犯罪现场”(病理切片)后,把它认为最重要的“线索”都标记出来。
分析“错案”:AI的失误并非无厘头
在静默试验中,研究人员专门分析了那些AI预测错误(即假阳性和假阴性)的案例。结果发现,AI的错误往往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深刻的生物学和病理学逻辑。
假阳性案例:原来是“近亲”。在一些案例中,EAGLE非常自信地预测“存在EGFR突变”,但最终的NGS报告却显示EGFR是阴性的。当研究人员仔细查看这些“冤假错案”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这些肿瘤虽然没有EGFR突变,但很多都携带了另一种名为ERBB2(也称HER2)基因的突变。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看,ERBB2和EGFR是“亲兄弟”,它们驱动的癌细胞在形态学上表现出相似的“视觉指纹”是完全合乎逻辑的。AI把“弟弟”错认成了“哥哥”,这揭示了模型能力的边界,也为未来训练更强大的AI提供了思路。
假阴性案例:原材料质量是关键。而在另一些案例中,肿瘤确实有EGFR突变,但EAGLE却没能识别出来。通过分析这些“漏网之鱼”,研究人员发现它们大多是细胞学样本、样本质量差或肿瘤含量极低。例如在一个案例中,NGS报告显示突变丰度小于5%,AI和人类病理学家一样,都面临着“大海捞针”的挑战。
这些“错案”的分析,给了我们两个极其重要的启示:第一,AI不是万能的,它的表现高度依赖于输入的“原材料”质量。第二,“人机协同”是未来的方向。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当AI对一份样本给出低分,但注意力地图却显示它在极少数可疑细胞上表现出“犹豫”时,系统可以向人类病理学家发出警示,从而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通过揭开“黑箱”,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冰冷、不可知的算法,而是一个可以被理解、被引导、能够与人类专家形成互补的强大合作伙伴。
当显微镜下的世界变得“可计算”
EAGLE模型的成功,尤其是其在前瞻性静默试验中的卓越表现,标志着计算病理学领域一个重要里程碑的诞生。它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AI不再仅仅是停留在论文和回顾性数据集中的“屠龙之技”,而是已经磨砺成能够踏入真实临床战场、解决实际问题的“倚天之剑”。
从单一靶点到“全景扫描”
EAGLE的成功,其意义远不止于EGFR突变检测本身。它验证了一套极具潜力的“方法论”:即“基础模型预训练 + 特定任务精细调优”的模式。这套方法论就像一个“AI兵工厂”,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针对不同分子靶点的“AI神探”。今天我们训练它识别EGFR,明天我们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训练能够识别ALK、ROS1等其他重要突变的专用模型。
未来,我们甚至可以期待更强大的“全能型”AI。它或许能在一张切片上,同时预测多种不同基因的突变状态,甚至预测肿瘤的免疫微环境、化疗敏感性、患者的预后等更复杂的生物学信息。病理切片,这张曾经只能提供形态学信息的二维图像,正在AI的赋能下,变成一个蕴含着多维度、深层次生物学信息的“数字矿藏”。
跨越鸿沟:让顶尖诊断能力“飞入寻常百姓家”
更深远地看,EAGLE这类AI工具,拥有着重塑全球医疗公平性的巨大潜力。在传统模式下,顶尖的分子病理诊断能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型癌症中心。而AI是数字化的、可复制的、可远程部署的。一个成熟的AI模型,理论上可以被部署到任何一个拥有数字病理扫描仪和基本计算能力的角落。这意味着,一位身处偏远小镇的肺癌患者,他的病理切片可以通过云端,由世界顶级的AI模型进行分析,在几十分钟内获得一个与大型癌症中心质量相当的预测结果。
AI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抹平地域和经济带来的医疗鸿沟,让最前沿的精准诊断能力,真正有机会“飞入寻常百姓家”。
人与机器,共赴未来
回到我们最初开始的地方——那个在等待中煎熬的患者。EAGLE的出现,为他描绘了一幅崭新的图景:活检之后,不再是遥遥无期的等待和对组织耗尽的担忧。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快速、精准、无损的AI预筛查,它像一位忠诚的向导,为后续的诊断和治疗之路指明了最有效率的方向,确保每一份宝贵的生命样本都能发挥其最大价值。
EAGLE的故事,是关于算法的,但更是关于人的。它展现了研究人员如何以临床需求为导向,巧妙地运用前沿技术,攻克现实世界中的难题。它也预示着一个“人机共生”的医学新范式:AI不会取代医生,而是将成为医生最强大的“外脑”和“鹰眼”,将他们从重复、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去完成那些更需要智慧、经验和人文关怀的创造性工作。
显微镜下的世界,曾经静默无声。而今,在0和1的交响中,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可计算”,充满了无限的可能。这束由人工智能点亮的黎明之光,正照亮着病理学乃至整个精准医疗的未来。而这条路的终点,将是为每一位癌症患者,带来更快速、更精准、也更温暖的希望。
参考文献
Campanella G, Kumar N, Nanda S, Singi S, Fluder E, Kwan R, Muehlstedt S, Pfarr N, Schüffler PJ, Häggström I, Neittaanmäki N, Akyürek LM, Basnet A, Jamaspishvili T, Nasr MR, Croken MM, Hirsch FR, Elkrief A, Yu H, Ardon O, Goldgof GM, Hameed M, Houldsworth J, Arcila M, Fuchs TJ, Vanderbilt C. Real-world deployment of a fine-tuned pathology foundation model for lung cancer biomarker detection. Nat Med. 2025 Jul 9. doi: 10.1038/s41591-025-03780-x.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0634781.
本网站所有内容来源注明为“梅斯医学”或“MedSci原创”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梅斯医学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为“梅斯医学”。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或“梅斯号”自媒体发布的文章,仅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站仅负责审核内容合规,其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不负责内容的准确性和版权。如果存在侵权、或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在此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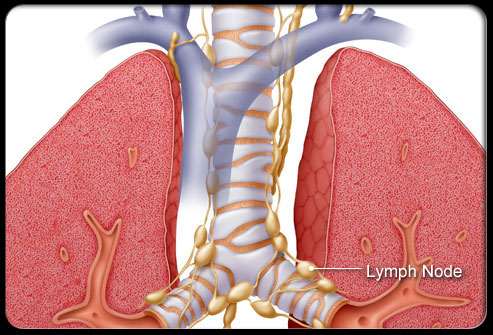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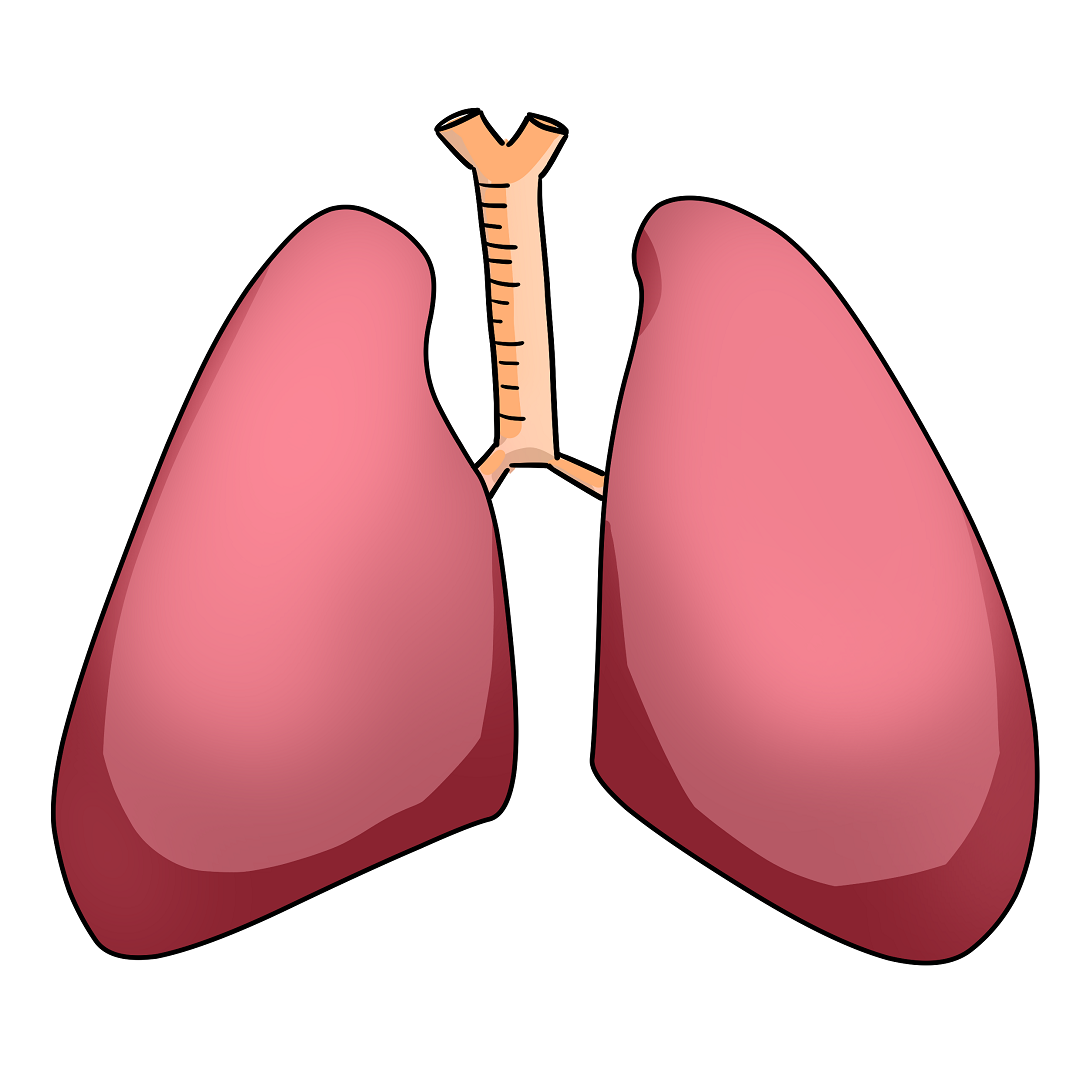






#肺腺癌# #EAGLE模型#
10 举报